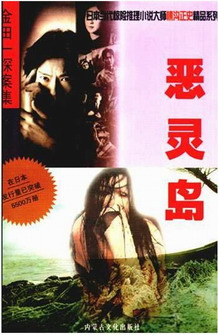古拉格群岛-第19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之所以需要一个清除了杂乱琐事的头脑,是因为我开始写叙事诗已经有两年了。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怎么能写诗呢?柯罗连科讲过他自己在监狱里也曾从事写作。但他那时的监狱里是怎样看管的呀!他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没有摸遍衣服的第一处折边,搜走他的铅笔呢?)铅笔是他藏在卷曲的头发里带进来的,(为什么没把他的头发剃光?)他是在嘈杂声中从事写作的。(快道声谢谢阳,因为你还有地方坐下来,把腿伸开写字呢!)何况此外还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狱外。(这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理解的!)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劳改营里,即使是在生活区的工棚里也不能这样写东西1(甚至你想为未来的小说拟几个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险。是黑组织名单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词形式记下来,或者把它变成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便成了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起初,我不大相信记忆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决定用诗的形式写。当然,实际上是强加于这种体裁的。后来,我发现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脑海中的奥秘压缩进去。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存储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还远远不够!
但是,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绝不使用整张的纸。.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这项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动火柴杆时嘴唇作出像是说话的动作或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就肯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怀疑。所以,我在移动火柴杆时尽量装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样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时候,我便特别把它记住,作为进行检查的标记。每月我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这时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
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我曾经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们自己制作一种狱里用的念珠。他们把面包用水泡开揉烂,染上颜色(用烧焦的胶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红药水染红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时候用细绳穿起来,那细绳是用线捻成后抹上了肥皂的。然后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我后来也加入了他们一伙,我说自己也想数着念珠祈祷。不过,按我信的宗教教规,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颗(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只要二十颗就够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软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颗不能是圆的,应该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颗和第一百颗也要有所区别,能摸得出来才行。立陶宛人虽然对于我这种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诚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颗),但还是深表同情地帮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颗珠子做成一个深红色的心形。我后来一直把他们这一绝妙礼物带在身边。冬天,我把它放在宽大的连指手套里,在派工地点,在从一处被赶到另一处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时刻,我不知数了它多少遍。这是站着就能作到的,天气多冷都不碍事。它就藏在这大棉手套里通过了各次搜查。有几次倒是被看守发现了,但他一看是祈祷用的,也就还给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结束(这时我写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来在流放地点,都多亏了这串念珠帮助我写作,帮助我记忆……不过,也并不那么简单。积累的诗句越多,每月复习所占的天数也就越多。特别是这种复习还有一个害处,就是所写的诗句背得烂熟了,就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优劣,无法提高了。为了尽快把纸片烧掉,本来就是匆忙中决定的初步方案,后来往往成为唯一的方案了。把写好的东西放起来,忘掉它,几年之后再取出来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这种奢望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不能把没有烧掉的小纸片久留在身边。有三次它曾给我带来很大危险。只因为我从来不把最危险的字眼写在纸上,而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才使我免遭灾祸。有一次,我为了安静,离开大伙儿独自趴在离营区障碍地带较近的草地上,把小纸片夹在一本书里伪装起来写诗。不料这时一个看守头头,鞑靼人,从我身后轻轻地走来了。他看见我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写什么。
“喂,拿来!”他命令我把小纸片交给他。我站起来,捏着一把冷汗把纸片送过去。那上面写的是:
定要补偿我们的一切,
要还我们,还要答谢。
我记得那步行的五昼夜,
从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
是K〔哈萨克人〕与T[鞑靼人'
驱赶着我们,〔担任警戒]
假如这上面的“按按人”和“担任警戒”几个字全写了出来,看守定会把我立即揪去见行动人员,他们就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略字和横线像哑巴一样,什么也说明不了,他看到的是:
是K——与T——
驱赶着我们,——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我在为自己的诗担心,可是他却以为我在画障碍地带的略图,准备逃跑。不过,他也没有放过这张小纸块。他踏着眉头反复读了好几遍。“驱赶着我们”几个字已经使他想到一些什么了,特别使他动脑筋的是“五昼夜”。我甚至没去考虑这几个字会引起他的什么联想!“五昼夜”——这是劳改营里关囚犯禁闭时说的标准用语。
“关了谁五昼夜?你说的是谁?”鞑靼人看守皱着眉头追问。
我好容易才借助“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两个名词使他相信:我是在回忆别人写的一首关于前线的诗,可怎么也想不起全诗来了。
“你干什么要回忆?不许回忆!”他拉长了脸警告我,“看你再敢躺在这儿!有你受的!
今天来谈这件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对于我,对于一个一钱不值的奴隶来说,这却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从此便不能再离开嘈杂的人声躲到一旁去写诗了。假如再叫这个按期人抓住,看到另外的诗句,就完全可能对我立案审查,加强监视。
而我现在已经不能丢掉写作了!……
还有一次,我违背了自己的习惯,在工地上一气写下一个剧本中的六十行诗,而且收工回营时没有把这一张纸藏好。当然,那上面许多重要的词也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的。看守是个宽鼻梁的小伙子,挺朴实的。他看着这猎获物有点奇怪。
“是写信吗?”他问道。
(把写好的信带到劳动工地,被查出来只不过蹲几天禁闭。但是,这封“信”要是落到行动人员手里,就会引起他的疑心了!)
“这是我准备演文艺节目的时候用的,”我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正在回忆一个剧本。演出的时候,您来看吧。”
小伙子的眼光在那张纸片和我的身上来回扫了几遍,然后说:
“身体倒挺结实,可是个混蛋!”
说着,他把我的纸片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块、八块……。我生怕他扔在地上,因为那碎片还是够大的,在这岗楼附近它很可能落到警惕性更高的长官手里,劳改营的长官马切霍夫斯基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搜查呢。但是,看来他们是规定不许到处乱扔东西的,弄脏了还得自己打扫。所以,看守就把撕碎的纸片像塞进字纸篓一样又塞在我的手里。我一进工棚门就急忙把它扔进了火炉。
还有一次,我手里还有一大段诗没有烧掉,可是,在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时候,抑制不住诗兴,我又写下了《砌石工》。那个时期我们是在隔离区内劳动,无须到区外去,因而对我们勿需每天搜身。我把《砌石工》带在身上已经两天了。第三天,晚点名之前,我想趁天色昏黑的当地到屋外去复习一次,然后把它烧掉。我想找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安静处,却不知不觉走近了障碍地带。没想到这恰好是不久前腾诺钻铁丝网逃跑的地方。一个似乎原来就埋伏在那里的看守立即揪住了我的衣领,在黑暗中把我带进了加强管制工棚。我利用在暗处走的工夫悄悄把《砌石工》揉成一团,扔在身后了。这时正刮风,看守没有听见我揉纸和扔纸的声音。
我一点也没想到身上还带着另一段诗。到加强管制工棚一搜查,把它搜出来了。幸而那完全不是什么犯罪的东西,是写前线生活的一段(《普鲁士之夜》中的一段)。
这位上士班长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读了一遍。
“这是什么?”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瓦西里·焦尔金》。”我坚定地回答。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两人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是第一次相交。)
“特瓦尔多——夫斯基!”上上含着几分敬意说,“你写它作什么?”
“这里没有书看。我就这样凭记忆写下来,有时候读上两句。”
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脸刀片——被没收了,把那小段诗还给了我。他本来可以放掉我。那我就会赶紧去寻找我的《砌石工》。但是,这时已经过了点名时间,囚犯们已不能在营区随便走动了。所以看守亲自把我送回工棚,锁上了门。
我一夜没有睡好。外面的风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会被刮到哪里去呢?尽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横线,但诗的大意还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内容就可以断定作者是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乌克兰人中间是不难找到我的。
因此,现在在营区某处或草原上无可奈何地被大风吹着到处滚动的不只是那个小纸团,而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是已经写出的,更重要的是计划要写出的全部东西。我呢,只有祷告上帝保佑。每当处境不佳的时候,我们向来是不以信奉上帝为耻辱的。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耻于信上帝。
早晨,五点钟,刚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着使人窒息的寒风跑到昨天扔纸的地方去找。狂风卷起砂石扑打着我的脸。哪里去找呢?风从这里吹向营部方向,再远就是惩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来来往往。还有几道交叉的铁丝网),再往前就是障碍地带,是小村镇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弯着腰来回找了整整一小时,毫无结果。我已经绝望了。谁知天刚亮,我看见就在离我扔纸团的地方三四步远处有一个白东西——风把小纸团吹到旁边,恰巧夹在地上的两块木板中间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我就是这样写作的。冬天,在工间休息取暖的时候写。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头上写。趁着两次抬灰浆的间隙,我把纸片放在砖上用铅笔头(还得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偷偷写下上一次抬灰浆时想好的一两行诗。我像是生活在梦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烂菜汤时,我常常确实“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见周围人的谈话,我总是在沿着自己诗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块块砖砌成墙一样砌造我的诗篇。人们搜查我,点名,报数,跟着队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却只看到我写的戏剧的场面、幕布的颜色、布景中的家具摆设、一排顶灯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
别的小伙子乘汽车冲出去,把铁丝网偷偷剪断,在大风雪里从一个雪堆爬向另一个雪堆。对我来说,这些铁丝网似乎并不存在,我仿佛始终处于自己的长久的、遥远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们发现不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