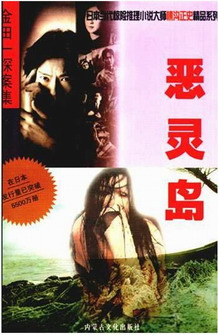古拉格群岛-第18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牢房里面我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但我内心却感到在他们面
前无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们抓进来的。他们都是些纯朴、勤
劳、信守诺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怎么会也落到这种绞肉机中
来了呢?他们没有招惹任何人,平静地过着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
社会道德比我们这里还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为他们住在我
们近旁而且挡着我们去海洋的路,他们就有罪了。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的时候,赫
尔岑就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着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
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我对拉脱维亚人的感情还要复杂得多。这里似乎有某种命运
之手在捉弄着我们。这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乌克兰人呢?我们已经很久不使用“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这个提法了,我们只说“班杰拉分子”,而且这个词在我们这
里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骂人的词了,以至谁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
的实质。(还有,我们使用“匪徒”这个词也是这样的。按我们习
惯的用法是:凡是为了我们而杀人的都是“游击队员”,而凡是杀
我们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农民在内。)
而问题的实质则是:尽管有过一个时期,在千年前的基辅罗
斯时代,我们大家确实曾经组成过统一的民族,但是,从那以后
这个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重新统一”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或许曾有人抱有过这种重新组织从前那种兄弟大家庭的真诚愿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能认真地想一想:怎样才能使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结成亲人,怎样才能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和创伤。(假如没有隔阂和创伤的话,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会组织什么乌克兰委员会,也不会有以后的“拉达”了。不过二月革命时期他们只要求实行联邦制,谁也没想分离出去。这种残酷的分裂肇始于共产党当政的年代。)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遇到困难。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过列宁的这样的话:“我们把乌克兰和别的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看作被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们所兼并的地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乌克兰已经组织起中央权力机构——中央“拉达”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还通过了一个《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该不是开玩笑的吧?当时这个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拥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权和自决权,那该不是欺骗人的吧?半年之后,苏维埃政府曾请求德意志帝国协助苏维埃俄国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宁同乌克兰黑特曼——斯柯罗帕德斯基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
但是怪了。德国人刚被协约国打败(这总不该影响我们对待乌克兰的原则吧1),黑特曼也跟着他们垮台,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同一血统的兄弟们身上。不错,在那以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我们曾不遗余力地、甚至是勉强地利用“莫瓦”——乌克兰的语言——大作文章,使那里的弟兄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完全独立的,而且是随时可以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的。但是,当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刚一表示想要这么作的时候,我们却宣布他们是“班杰拉分子”,并开始追捕、拷打并处决他们,或者把他们关进劳改营了。(其实“班杰拉分子”也和“彼得留拉分子”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在异族政权统治下生活的普通乌克兰人而已。当他们了解到希特勒也并不给予他们曾经许诺的自由时,他们便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同希特勒作战。但是,我们对这一点却缄口不言,因为提这一点对我们不利,就像我们从来不提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一样。)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即我们的兄弟们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讲话,用它教育孩子,写商店招牌,这为什么会使我们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他的小说《白卫军》中)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感情的影响。既然两个民族过去没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们之间有不同之处(只要他们,少数人,有这样的感觉就够了),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既然错过了时间,——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错过的,双方关系主要不是在沙皇时代而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尖锐化的!——他们要分离出去。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是舍不得敖德萨的海滨浴场?舍不得切尔卡塞的水果?
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很痛心的,因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里,都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者的结合。但是,在劳改营里同乌克兰人的长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们为此痛苦了多么久啊!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为老一代人的错误付出代价。
跺着脚喊叫:“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说一句:“谁想生活,就让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在二十世纪末
期,我们不应该仍旧生活在使我们最后那位不太聪明的皇帝伤透
脑筋的那个空想的世界里了。不管看来多么奇怪,但事实是:“先
进学说”关于民族主义正在衰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原子和控
制论的时代,它——民族主义——不知为什么反而兴盛起来了。这
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履行我们
关于自决权和独立的全部诺言。而且我们应该主动地使它兑现,不
要等待别人在火堆上烧死我们,在河里淹死我们或者砍掉我们的
脑袋。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我们不能靠疆土之广大,被保护民族之众多来证明,而只能靠行动之伟大来证
明,还要靠我们放弃了那些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后在
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来证明。
对乌克兰的处理将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现在就应该看到总
的发展趋势。既然过去多少世纪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就是
说,该是我们来表明自己明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交给他们自己
去决定。是交给联邦制派,还是交给分立派?那就要看他们之间
谁能说服谁了。不让步,则是愚蠢,是残酷。我们现在越是温和、
忍让和通情达理,那么将来重新恢复统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让他们自己生活,自己去试试吧。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分
离出去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
不知为什么,让我们在长长的马棚车房里住了很长时间,没
往斯捷普特种营押送。自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在这里很愉快,到了那里只会不如这里。
我们这里也不乏新闻消息,每天都有人拿来半张破报纸。常常是我念给全屋的人听,而我总是带着感情念,那里也确实有应该带着感情念的东西。
那些日子正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解放十周年纪念。我们牢房里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中间有些人懂俄语,他们把这些消息翻译给别人听(这时我就稍停一停)。当那些人听到在他们的国家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了怎样的“自由和繁荣”的生活时,他们竟失声痛哭起来了,上下铺的人一齐大哭。这些从波罗的海沿岸来的人(他们占整个递解站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每人都丢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不,如果还有“家庭”,那就算是不错的了,有些人的“家庭”也正在跟着另一批押解犯人被同样地押往西伯利亚。
但是,最使我们这些递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动的当然还是关于朝鲜的消息。斯大林的闪击战在那里失败了。联合国的志愿军已经召集起来。我们把朝鲜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班牙。(很可能斯大林就是把它当作第三次大战的彩排而开始的吧。)特别使我兴奋的是联合国的士兵们:看,他们那个旗子多有意思!这个旗帜什么人不联合呢?它简直是未来的人类总体的雏形!
使我们厌恶的是,我们不能有比厌恶更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死掉也不要紧,只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着我们死亡而无动于衷的人们能够安然无恙就行!”——难道我们能够这样想吗?不能,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绝对不能!我们确实在渴望着暴风雨的来临!‘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无耻的、绝望的思想呢?你们难道没有想到在监狱外面的广大人民要遭受战争灾祸吗?!”“但是,狱外的人们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过我们呀!”“那么说,你们怎么啦?竟然希望爆发世界大战?”“可是你在一九五O年就给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么他们除了希望发生世界大
战之外还能希望什么别的呢?”
现在,当我回忆起当时我们那些虚幻而有害的希望时,自己
也感到荒唐。全面的核毁灭不管对谁来说都不是出路。何况,即
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种战争状态都只能成为国内暴政的借口,会
加强国内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讲出真实情况,不说出我们在那
个夏天的实际想法,那么,我写的历史就被歪曲了。
罗曼·罗兰那一代人年轻时曾因为担心战争爆发而苦恼,而
我们这一代囚徒则相反,我们是因为没有战争而苦恼。这就是政治犯特种劳改营当时的真实精神状态。我们就是被逼到了这种地
步。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只会是两种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
来(从炮楼上扫射我们,像德国人干的那样在我们的食品里放毒
和使用杆菌),或者,也许会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
迅速地得到解脱,总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满期好些。
彼佳·帕…弗就是这样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们牢房里从
欧洲回国的人中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有牢
房里塞满了像他这样从欧洲回来的质朴的俄罗斯人,但是,那时
候回国的人早都已进了劳改营或者入土了,没回来的人也都下决
心不回来了。可是这个彼佳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正常人谁都不再回国的时候,自愿回到祖国来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哈尔科夫市的职业学校学习,他是战
时强迫动员到那里去学手艺的。不久,德国人来了,又把他们这
帮半大孩子强迫送到了德国。他这个“东方奴隶”在那里一直呆
到战争结束。他在那里养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人应该尽量使
生活过得轻松些,不要像自己小时那样被人强迫去劳动。在西方,
他利用了欧洲人的轻信态度和边境控制不甚严紧的状况,把法国
的汽车开到意大利,再把意大利的车开到法国,减价出售,从中
谋利。但是,他在法国到底还是被查出来,他被捕了。这时,他
给苏联驻法大使馆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回到他亲爱的祖国去。帕一弗当时是这样盘算的:如果蹲法国监狱,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后一天,而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苏联呢,他由于叛国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滂沱大雨已经开始落雨点了。而苏联呢,据他说,开战后连三年也保不住。因此,还是去苏联监狱更有好处。大使馆的朋友们自然是很快就来接收他了,并且拥抱了彼佳·帕一弗。法国当局欣然同意把这个盗窃犯移交给苏方。大使馆里集结了大约三十名像帕一弗这样的和有类似情况的人。使馆把他们用轮船舒舒服服地运到了苏联的摩尔曼斯克。靠岸之后,放他们到市内去游逛游逛,然后,就在一昼夜之内又把他们一个个全都逮捕起来了。
现在,在我们牢房里,彼佳能够代替西方的报纸(他曾仔细阅读过西方报刊关于克拉夫琴科案件的报导),也能够代替剧院(他可以轻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乐)和电影(他给我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