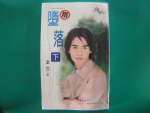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5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力的那一部分来说的。没有人会带着对赦免的内在确定性去自行忏悔。由于心灵仍跟以往一样迫切地需要从过去中摆脱出来,所有高级的交流形式都被用上了,而在新教国家中,音乐和绘画、书信和纪事,都从描绘的方式变成了自责、悔罪和漫无边际的忏悔的方式。甚至在信奉天主教的地区——尤其是在巴黎——当对忏悔和赦罪的圣礼发生怀疑时,也就开始把艺术当作心理学了。对世界的看法迷失在自身内部无尽的自我斗争之中。同时代的人和子孙后代都被召来充当教士和法官,以取代无限的位置。个人的艺术——在用以区分歌德和但丁、伦勃朗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意义上——成为告解的圣礼的替代品。这也表明这种文化已经处于晚期的状态。
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3)
四
在所有的文化中,宗教改革皆具有相同的意义——使宗教回复到其原初观念的纯洁性,就像其在初始的伟大世纪里所呈现的那样。没有一种文化不曾出现过这种运动,不论我们对之是有所了解,比如在埃及的情形中,还是无所了解,比如在中国的情形中。进而,这还意味着城市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城市精神逐渐摆脱了乡村的心灵,它在与后者的无限权力的抗衡中确立了自身,并开始参照自身当时的自我而重新思考原始的前都市时期的情感和思想。在麻葛世界和浮士德世界中,那在这一点上催生新宗教之萌芽的,正是命运,而不是思想的理智需要。今天,我们知道,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路德差一点就成为了整个不可分割的教会的改革家。
因为路德,像所有文化中的一切改革家一样,在从空旷的大地上伟大的苦行者到城市僧侣的巨大系列中,并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宗教改革是属于哥特式的,它的完成和圣约书(testament)亦是如此。路德的众赞歌(chorale)“上主是我坚固保障”(Ein’feste Burg)其实并不属于巴罗克式的灵修抒情诗。在那里面,仍然鸣响着圣歌《震怒之日》(Dies irae)的那种庄严的拉丁风格。它是“战斗教会”最后的强有力的撒旦之歌。路德——像从1000年以来出现的每一个改革家一样——对教会的斗争不是因为教会要求太多,而是因为它要求太少。这改革的洪流自克吕尼(Cluny)流出:通过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他宣传回到使徒的朴素生活,并在1155年被处火刑;通过弗洛里斯的乔基姆,他第一个使用了“reformare”(改革)这个词;通过方济各修会的圣徒;通过托底的雅各波内(Jacopone da Todi),这位革命者和《圣母悼歌》(Stabat Mater)的歌者,由于年轻妻子之死而遁入空门苦修,并因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治理教会过于松弛而力图将其推翻的骑士;再通过威克利夫(Wyclif)、胡斯和萨沃那洛拉;直到路德、卡尔施塔特(Karlstadt)、茨温利(Zwingli)、加尔文——以及罗耀拉。所有这些人的意图,都不是要去征服哥特式的基督教,而是想使它臻于内在的完善。同样的情形,在马西昂、阿泰纳西乌斯、一性派和聂斯脱利派那里也有发生,他们曾在以弗所和卡尔西顿公会议上力图纯洁信仰并引导它回到其源头。但同样地,公元前7世纪古典的奥菲斯派也是甚至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出现的那一系列教派中最后的而不是最初的一个。同样地,在埃及,古王国结束时即埃及哥特时期的拉教的建立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所表明的只是一个结局,而不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正是如此,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时,吠陀宗教中也发生了一次改革和完善的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晚期婆罗门教的建立。而在公元前9世纪时,在中国的宗教历史上,必定也曾发生过一次相应的时代转折。
不论各种文化的宗教改革彼此之间的差别是多么之大,但其目标都是一样的——把偏离正道太远而误入了作为历史之世界和时间世俗主义(time…secularism)的信仰引回到属于自然、纯洁的醒觉意识的王国和纯粹为原因所控制、为原因所充斥的空间之中;从经济(“财富”)的世界返回到科学(“贫穷”)的世界,从贵族和骑士的社会(这也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社会)返回到圣徒和苦行者的社会;最后(重要的是,它同样又是不可能的)从道貌岸然的人中才俊的政治野心返回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圣因果关系的王国。
在那些时代里,西方——在其他文化中情形也是一样——把居民的基督教团体分成政治阶层、教士阶层和经济阶层(即市民)三个等级,但由于这种观点属于城市而不属于城堡和乡村,因而官吏和法官属于第一个阶级,有学识的人属于第二个阶级——农民则被遗忘了。这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对立的关键,这种对立是一种阶级对立,而不是像文艺复兴和哥特文化之间那种在世界感上的差别。城堡趣味和修道院心灵被搬进了城镇,并且在那里跟以前一样依然处在对立之中——例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与萨沃那洛拉的对立,又如古希腊的城市贵族(以及他们的今天终于传下文字的荷马)与最后的奥菲斯派(这些人也是作家)的对立。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是抒情诗人和吟游诗人的合法传人,并且正像从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到路德一脉相传一样,从波尔那的贝特朗(Bertrand de Born)和皮尔·卡丁那尔(Peire Cardinal),经彼特拉克(Petrarch)到阿利奥斯托(Ariosto),也有一条脉络贯穿着。城堡已经变成市镇的房舍,骑士已经变成贵族。整个运动都依附于朝廷的宫邸;它把自身局限于旨在感染上流社会并使之发生兴趣的表现领域;它是明朗而快乐的,就像荷马一样,因为它是宫廷的——在那样一种氛围中,问题都属于低级趣味,在那里,但丁和米开朗基罗都不免感到无地自容——它还作为一种新的趣味而不是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越过阿尔卑斯传布到北方的朝廷之中。属于商业城市和都城的“北方”文艺复兴,不过就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即意大利贵族的上流社会替代了法国骑士的上流社会。
但是,这些最后的改革家,路德们和萨沃那洛拉们,也是城市僧侣,这使他们与乔基姆们和伯纳德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的智性的和都市的苦行,不过是从幽静山谷的隐修住所搬到巴罗克时代的学者书斋的跳板。使路德产生释罪教义的神秘体验并不是圣伯纳德的面对山林星空的体验,而是一个从狭窄的窗间向街头、墙壁和山墙看望的人的体验。上帝遍在的广阔的自然远居于城墙之外;脱离了土地的自由的心智却居于城墙之内。在城市的、为石墙所包围的醒觉意识里面,感觉和理性彼此分开并且变成了敌人,因此最后的改革家的城市神秘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纯粹理性的神秘主义,而不是一种内省的,亦即一种概念启发的神秘主义,面对这种神秘主义,古代神话中那些光彩照人的多姿形象将变得黯然失色。
因此,从其实际的深度看,这种城市神秘主义必然是属于少数人的事物。以前甚至对最穷苦的人也能提供某些可把握的东西的那种可感觉到的内容,现在什么也没有保存下来。路德的强有力的行为是一个纯理智的决定。作为奥卡姆路线最后一位伟大的经院学者,他并不是无可称道的。他彻底地解放了浮士德式的个性——僧侣的从前处于这个性与无限之间的中间人地位被取消了。现在,它完全是单独的、自我定向的,它是自己的神父,是自己的法官。但是,一般人只能感觉到而不能理解存在于个性之中的解放因素。诚然,他们是热烈地欢迎可见义务的撕毁,但他们未能认识到这些义务已经被甚至更加严格的理智的义务所取代了。阿西西的方济各是予多取少,而城市的宗教改革是取多予少,至少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
路德用“因信称义”而取得内心赦罪的神秘体验来取代忏悔圣礼的神圣因果关系。在悔罪这个概念上,他和明谷的伯纳德的看法是十分接近的,即认为悔罪是毕生要做的,是持续的理智的苦行,与重在外在的、可见的事功的苦行截然相反。他们两人都把赦免理解为是一种神迹:只要人自己在悔改,那就是上帝在改变他。但是,任何纯粹理智的神秘主义都无法取代那在外面的、在自由的自然之中的“你”(Tu)。这两人都说过:“你必须相信上帝已经宽恕了你”,但是,对于伯纳德来说,信仰是通过僧侣的力量而提升为知识的,而对于路德来说,它却要经过怀疑和不懈的坚持。这个脱离了宇宙、被安置在个体存在之中、并且孤独的(在这个词最可怕的意义上说)和渺小的“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你”的接近,而且理智越是脆弱,那需要就越是迫切。这里就是西方僧侣的根本意义所在,他们从1215年起就通过受令行使圣礼及其不可消除的特性而被提升到其他人之上:他们就是一只手,连最可怜的人也可借之而把握到上帝。同无限的这一可见的联系被新教完全摧毁了。强大的心灵能够也确曾为自己赢回过它,但对于比较软弱的人来说,这一联系已逐渐地消失。尽管对于伯纳德来说灵性的奇迹有凭借自己成功的时候,但他并不排除他人可以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因为他的心灵的开悟已经向他敞现了无所不在、永远接近、永远有所助益的活生生的自然的马利亚世界。路德只了解他自己而不了解人,他树立了一种假想的英雄主义以取代人的实际弱点。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与魔鬼的生死决战,他呼吁每个人都投入这场战斗。而每一个投入战斗的人都是各自为战。
宗教改革废除了哥特式神话整个光明的和慰藉的一面——对马利亚的崇拜,对圣徒、圣物的敬奉、朝圣、弥撒。但是,魔界和魔法的神话依然存在,因为它是内心痛苦的体现和原因,并且有时这种痛苦会最终上升为至大的恐怖。洗礼,至少对路德而言,是一种驱魔术,一种驱除魔鬼的真正圣礼。关于魔鬼,已出现了大量的纯粹新教的文学作品。从哥特文化的丰富色彩中,只保留了黑色;从它的艺术中,只保留了音乐,特别是风琴类的音乐。但是,在神话中光的世界的所在——其有所助益的接近毕竟是一般人的信仰所不愿放弃的——又从长久掩埋的深处涌现出了古代日耳曼神话的要素。它来得如此隐秘,以至甚至今天,它的真正意义还未被认识。“民间故事”和“民众习俗”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它是真正的神话,就存在于对侏儒、妖魔、水怪、宅鬼和如乌云般吹过的亡魂的坚定信仰中;它也是真正的崇拜,在一直怀着虔诚的敬畏而施行的仪式、献祭、召神中都可以见到。在德意志,无论如何,英雄传奇已不知不觉地取代了马利亚神话的地位:马利亚现在被称作荷德夫人(Frau Holde),而在圣徒曾经站立的地方,则出现了虔信的艾克哈特。在英国人当中,则出现了长期以来称作“拜圣经派”(Bible…fetishism)之流。
路德所缺乏的——这也是德国永恒的不幸——是对于事实的观察力和实际组织的能力。他没有使他的学说形成一个清晰的系统,也没有领导这个伟大的运动并为它选定目标。这两者都是他的伟大的继承者加尔文的事业。当路德派运动在中欧群龙无首的时候,加尔文把他在日内瓦的控制权视作是以新教的名义有系统地征服世界的出发点,他断然地认定此乃是新教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他,而且只有他,成为了一个世界权威;因此,正是加尔文精神和罗耀拉精神之间决定性的斗争,自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就支配着巴罗克时期的世界政治和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当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在中欧为了争取一些小的帝国城市或瑞士的一些贫瘠的州而展开斗争时,加拿大、恒河河口、好望角、密西西比等地都成为法兰西和西班牙、英格兰和荷兰为解决争端而进行大决战的场所。并且在这些决战中,西方晚期宗教的这两位伟大的创建者一直是在场的,且一直是对立的。
五
晚期的理智创造不是始于宗教改革,而是始于宗教改革之后。其最典型的创造就是自由的科学(free science)。甚至对于路德来说,学问实质上仍是“神学的婢女”,而加尔文还将自由思考的塞尔维特(Servet)医生送上了火刑场。青春时期——浮士德文化的与埃及文化的、吠陀经的和奥菲斯教的青春时期都一样——的思想觉得它的使命就是通过批判来证明信仰的合理性。如果批判失败,则批判方法必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