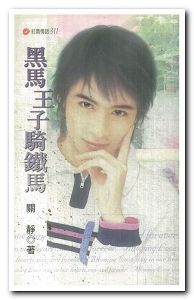金戈铁马-第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朕……”被催促,太仪不经考虑的武装起自己,拒绝的话尚未出口,头上复杂的发髻一松,花簪步摇掉了一地。
天朝虽然男女平权,但风气并非开放,女子在人前是不得披头散发的,那等同在众人面前赤裸着身子。
熟知礼教的太仪当场傻了。
他绝对是故意的!
既然不给她拒绝的余地,何不一开始直接命令算了?
“这下麻烦了,孤对女人家的玩意儿向来不上手,拆还拿手些。”仲骸意有所指的说。
亲近的部将听到,都笑了。
其它排在后头的群臣互觑了几眼,只得跟着笑。
帝王懦弱至斯,天朝的未来在哪里?
恐怕要不了多久,帝家将有姓仲。
她瞪着他,他则满不在乎的模样。
没听过胜者需要在乎手下俘虏的心情的。
“内侍,护送主上回寝殿。”仲骸一声令下。
内侍上前,簇拥在太仪身边,迅速收拾满地的钗簪。
太仪一整天红潮不退的脸,此刻恼羞成怒,提起厚重的裙摆,勉强维持皇族的骄傲,转身离去。
捧着发簪金钗的内侍连忙朝仲骸敛礼,追了过去。
“主公何不把话说清楚?”目送太仪怒发冲冠的背影,向来仁慈的房术忍不住叹了口气。
想也知道,他这个满肚子心计,有话不会明说的主子,不过是希望主上能回寝殿好好的休息。
仲骸勾起嘴角,不答反问,“难道你忘了是孤要她寸步不离,逼她即使抱病带伤也得跟来?”
即使被道中心思,他也不愿承认。
“主公想惩罚主上昨夜的失态,应该在主上对雕像的事退让时,便适可而止。”房术不赞同的摇头。
“主上是需要被强势对待的那种女人。”声音沙哑难听的孙丑倒有不同见地。
仲骸帐下的两大军师中,一屯田安内,一用计征外。前者房术宅心仁厚,擅长游说,带兵善守;后者孙丑完全相反,工于心计,用兵善攻。
他们是仲骸帐下的两大制衡势力。
“太强势,她又会反咬你一口。”仲骸莞尔的揶揄。
“昨夜的事我听说了,主公吃鳖了吧!”仲骸手下部将伏悉嘻笑的说。
他看起来和仲骸差不多年纪,背上背着双刀,而非一般骑马的将领那样用攻击范围较长远的武器,额上戴了一圈简单的环,上头铸了“佑主”两个字。
仲骸瞥了他一眼,“果真是坏事传千里。”
“也没到千里啦!昨夜守寝殿的侍卫刚好是我的手下,他们总得向我回报情况。”
“看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们还分辨不清。”
仲骸重新迈开步伐,群臣又跟着他移动。
“我只告诉他们,有危主公性命的事一定要告诉我。”
“孤在你心中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那真是侮辱。”仲骸失笑,不怎么认真的指责伏悉。
“主公不是对付不了女人,是特别偏爱麻烦而已。”孙丑暗笑。
“我以为主公偏爱的是美女。”伏悉不以为然,却赞同部分的话,“但主上确实是个麻烦。”
仲骸知道,某些部下和孙丑一样,认定留下太仪会是个麻烦。
“房术,你说呢?”他转问另一名尚未表态的军师。
“主公没有偏爱,而是爱天下男人都爱的东西而已。”房术神态轻松,说出来的话却扑朔迷离。
被道中心思,仲骸不住的颔首。
“还是你了解孤。”
“什么意思?”伏悉有听没有懂。
孙丑则是想了一下,便了解真意。
房术但笑不语。
伏悉只好看向孙丑。
“等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就会知道了。”孙丑的声音沙哑。
权倾一时的男人最想掌握的两样东西为何?
不就是江山和美人而已。
伏悉却还弄不清,兀自喃喃自语。
“主公,孙丑必须提醒您,越漂亮的花,若不是生在难采的孤岭绝境,就是含有剧毒尖刺,都会伤人。”孙丑确实认为太仪是个麻烦,但不认为是个无法解决的麻烦,困难些罢了。
“采花这种工作,向来是见猎心喜的人会做的事,孤喜欢的是种花。”仲骸慢条斯理的开口。
“而种花是别有所图的人会做的事。”房术接着说。
深邃的眼敛起,仲骸露出若有似无的笑容,拿定主意。
“主簿,拟旨。”
第2章(2)
太仪回房后,气得喘不过气。
内侍匆忙宣来医官,折腾了好一阵子,才缓下她上气不接下气的毛病,却安抚不了她心头狂炽的愤怒。
几乎咬碎一口白牙,她还是极为沉着的屏退宫女,更让人弄熄所有烛火,独留一盏小灯在床边。
生平第一次,她发现了凌驾在病痛上的,是对一个人的愤怒和怨怼。
主上,仲骸来接您了……
宫破那天,她在深夜惊醒,被平常随侍的宫女披上过大的黑色披风,希望能藉由天色的掩护,帮助她顺利逃过此劫。
她不知道自己在极阳宫里乱窜了多久,只知道周围的人越来越少,直到面对那个扮相极为寻常,连兵器都没带的男人时,她的身边已经没有半个能够保护她的人。
还记得当时她紧紧握着揣在胸口的匕首,盯着那个看似寻常,在战场上却是异常的人。
只要他一有动静,就给他一刀。
他也看着她。
左脸被头发覆盖,可右眼清亮澄澈,不知是否远处的火光烧进了他的眼底,她见到了耀眼的光芒在里头跳跃。
虽然不应该,她却被他的眼吸引了。
一生中,头一次产生好奇的对象,是砍下父皇的脑袋,对着她喊“主上”的挟持者。
那天起,她把“仲骸”这两个字深深的刻在心头,没敢忘。
即使有人说他是代天行道,除去乱朝纲的九侍和昏庸无道的软弱先帝,即使民心的向背落在他身上……不能忘,她怎么能忘记手刃父母的仇人?
微弱的烛火摇曳,投射在她布满泪痕的脸上。
突然,一只手探上太仪饱满的额头,专注到没发现有人的她因为惊讶,浑身颤了一下。
“风寒。”仲骸坐在蓬松的羽被上,替她拨开微湿的发丝,换了块降温用的布巾,“料想中的事。”
太仪没有白费工夫去拭泪,直接当作没看见他,用力转身,任由新换上的布巾掉落在枕边。
“唔……”没想到脑袋还很重、很顿,这么一个动作,就让她头昏眼花,反胃了起来。
太仪捂住嘴巴,怕在他面前露出丑态,但已经隐忍不住。
似乎看出她的难受,仲骸想也不想的伸出手,放在她的面前。
她来不及表现惊讶,压不下的反胃已经烧向口腔。
一时之间,安静的寝殿内,只有她喘息呻吟的声音。
她吐了,而且吐了他一身。
仲骸没有闪躲,让她吐完不舒服的感觉,才慢条斯理的整理起两人的混乱。
他替太仪换下衣袍,擦拭狼狈,仿佛理所当然,没有嫌恶。
她却哭了,咬紧牙根的低泣,几乎只剩鼻息。
在最恨的敌人面前如此羞愧和难堪,逼得她忍不住羞愤的眼泪。
手上的动作一顿,仲骸当作没有看到,继续擦拭,顺着白皙的腹部向上。
她的手捏成拳,捶了一下床。
仲骸的手又向上。
她又捶了一下,比前一次还用力,屈辱的泪水不断的滑下。
他敛下眼眉,用旁边备着的清水洗净布巾,装作未被她的眼泪影响,却无法欺骗自己不断涌上的抑郁。
难道让他窥见她不堪一击的一面真有如此难堪?
当他的手重新回到她身上时,太仪早已闭上双眼,感觉耻辱,不愿再去看自己有多狼狈。
她越哭,他的手劲越轻。
“哭什么?”他不懂自己明明不想听,却又逼她说的心思。
面对这个女人的眼泪,他常常乱了套。
她咬着牙,不肯言语,怕泄漏了哭声。
他的手已然来到少女浑圆的软丘,稍微停驻,最后还是向上。
“难道孤待你不好?”他的手不带挑逗的意思,眼底却燃烧着暗火。
“难道朕还有选择?”她哑着声音,死也不肯睁开眼。
她恨自己如此的无助,竟连阻止他也做不到。
仲骸一语不发,以更为缓慢的速度,清理妥当后,帮极不情愿的太仪穿上新的睡袍,才处理自己身上的污秽。
“你只是不明白什么样的抉择才是最正确的。”
“朕错在助纣为虐,如今只能一错再错。”她剧烈的咳了起来。
仲骸拿来水杯,却被她一掌挥开。
双眼瞬间凛起,他仰头喝掉剩余的水,迅速来到她的面前,捧起她的脸,就口,将清水悉数喂进她的口中,然后抬高她的下颚,逼她不能吐出来。
“那么,就继续错下去吧!”
如火的双眸死瞪着他。
确定她吞了下去,仲骸才让她躺回床上,拾起布巾,再度盖在她的额头上。
太仪扭动着,犹不肯从,仲骸的意志力同样坚定,使力逼她就范,费了好大的工夫才如愿以偿,这次手再也没拿开。
双手抱着自己,闭上眼,太仪等着他自讨没趣的离开。
孰料他吭也不吭一声,维持这个动作好半晌,连嫌酸换手都没有,倒是她渐渐意识到他这样的举动,看似强迫,却从头到尾没有弄伤她半分后,到随着时间过去,越感别扭。
仲骸不该是这样。
他总是尖酸刻薄,逼她认清现实,为何现在要对她好?
“不反抗了?”
他的声音靠得很近,太仪猛地睁开眼,就见他垂头凝视着自己。
又是深不见底的黑,却令人心慌意乱。
看清他的专注,她的心跳因染上彼此的深息而失速。
原本只是想弄清楚的仲骸注意到她不同于平常的反应,深幽的眼眸微凛,涌窜起青蓝的光芒,火炬一般耀眼。
她慌了。
“主上。”
他的轻喃像是警讯,太仪不禁闭上眼,扭开螓首。
“看着孤……”
仲骸轻声诱哄,太仪睁开眼片刻,又闭上,坚持不看他,于是修长的指头滑上她的胸前,温厚的掌心紧贴着浑圆的隆起。
“你……”她诧异的睁开眼,不能确定是不想被发现心跳的速度,还是害怕他越界的碰触。
他立刻强势的吻住她。
仲骸的吻如同他的人,时而狂放,时而温文,难以捉摸,又引人沉溺。
男性强而有力的气息撩拨着最柔软的女性部分,烧了镇日的体温,因他而无限攀升,没有终止。
当腰被宽大的掌拱起,紧贴着他的上身,唇舌相触的过分亲匿感融化了脑浆,原本虚软无力的身躯更加松散,她的腰已经无力到仿佛不是自己的。
昨夜的他是那么的可恶,不让她见风曦,也不肯放她离开,她是如此的恨他,曾经连见也不想见到他。
为何现在他正亲吻着自己?
怎么他看起来没有昨夜那么可恶?
仅仅一夜,他的面容怎么会有所改变?
或者,改变的是她意志不坚定的心?
“这就是你想要的?当朕病得昏头转向时,乘乱使坏?”她在换气的空档,迸出了讥诮的言词。
仲骸顿了顿,眼底的蓝光消失,随后退开,不置一词。
身上的温度骤失,她突然感觉夜是那么的寒冷,下意识的抓起羽被盖住自己,想隐藏失态。
仲骸背对着她坐了一会儿,又回头替她换了一次布巾,探她的体温。
太仪默默的注意他的每一个动作,等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冷嘲热讽,却什么也没有。
今夜,他特别宽容。
“请主上好好的休息。”这是仲骸在她的床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接着起身离开。
望着他的背影,她伸出手想捞回什么,但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捏紧拳头,她低声问道。
他的步履暂停,转身,“嗯?”
“为何待朕这么好?”疑惑、不解、猜测,她的眼底表现了这些情绪。
“不过是替换湿布巾这种事,难道没人为你做过?”仲骸不具恶意的反问。
她的心在无意间被刺痛了。
没有。
没有她在意的人做过。
“你可以走了。”她转身,不再看他。
仲骸停留片刻,瞅着那抹纤细易碎的背影,许久,然后转身。
侧耳聆听,足音逐渐远去,最后消失,她闭紧了眼,浇熄心中的暗火。
也好,她不该为敌人乱了心。
不该的。
不该为一个女人乱了心神。
仲骸走在回房的路上,心烦意乱。
他是个天生的战士,出生就在战场。
被敖戎收为家臣之前,他在战场上靠着捡拾武器,甚至食人肉维生。敖戎在尸骸中发现了他,因为他身上背着被灭的仲氏的刀,于是敖戎将他命名为仲骸,奠定了他武将的一生。
他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