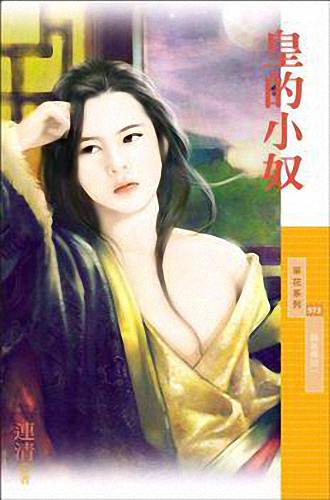小奴有礼-第1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做何手段;段负浪的身份也是风雨飘零中,随时可能暴露;还有彝族,伺机在动,难料凶险。
若密所真能远离这一切,也不失为一件庆事。
他想得太美了。
他顾虑的一切尚无进展,然他极力想让危机同她撇开的人却很快便出了事———密所笃诺因毒杀大理王朝至高无上的王上及储君殿下两位贵主儿被打入鬼字号地牢,死路一条!
这个消息传来,李原庸如遭五雷轰顶。
她怎么这么糊涂啊?竟然跑去毒杀王上同储君殿下?!
即便彝族逼她逼得紧,她若执意不为,有高泰明为她撑腰,彝族之人也不能拿她如何啊!如今,她可真就是死路一条了。
他躲着避着让着拒绝着,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图她个平安。可到底呢?到底还是将她推进了死牢。
哈,多年前,为了换回一个人一生的平安,他自愿来大理为暗桩;多年后,又是为了换回一个人的安宁,他宁可永远地孤寂下去。
结果呢?
他想守护的第一人,竟自动现身大理,主动放弃安逸的日子;他想守护的第二人被打入死牢,彻底断了生路。
那这些年,他付出的一切终究是为了什么?
不行,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他得救她,舍弃一切也当救她。
此刻,唯一可以救她的只有这大理王朝至高无上的王上———段素徽。
李原庸跪在大正殿寝宫门口已跪了足足两个时辰,可王上就是不见他,让他满腹救人之念憋得越发难过。
他求王上身边的宫人:“长宫人,烦请你再去呈禀王上,李原庸当真有紧要之事亲禀王上。”
长宫人只回说:“王上病重,正服汤药昏睡之际,发了话了,谁也不见。”
这话李原庸一连听了两日,今日他是再听不下去了。趁着长宫人闪神的当口,他脚下生风,不等通禀便蹿进了寝宫之内,吓得长宫人连声大喊:“来人啊!快来人啊,李将军闯宫!李将军闯宫了———”
众侍卫一齐涌上,欲将李原庸擒服。他的功夫可不是唬人的,于少年时便能以一敌百杀出重围,成为耀王爷的贴身守将,这些年的修为更是让他的功夫于宫中无人能敌,随便几招便丢下众侍卫,闯到王上身边。
见到段素徽,他顿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顺势匍匐在他的脚下,“王上赎罪,臣确有紧急之事,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
段素徽挥挥王袖,让一干人等退下,只留李原庸同他独自相对,长宫人不放心,张了张口刚要提醒,段素徽先道了:“李将军有事求孤王,断不会加害孤王的。”
他什么都明白,李原庸也就不必再兜圈子了,“臣……臣望王上格外开恩,饶……饶了那侍婢一命。”
“孤王本不欲要她的性命,李将军不必担心。”
他倒是大度,大度得很,对一个欲取自己性命的侍婢还不欲行刑———真乃君王之海量也。
他越是如此,李原庸越是害怕。怎么可能对一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处之泰然呢?定是有所计划的,单不知王上打算如何利用密所。
这个不妨,段素徽明着告诉他:“孤王不仅要留着她,还要好好地留着她,她这一条命牵动的人心可就多了去了。近,有你冒着闯宫死罪为她求情;远……先前忙忙碌碌的一支人马如今倒安稳了下来———她如此重要,孤王怎能轻易要了她的小命?”
摆明了王上已有了谋划,只怕密所活着比死还难。李原庸长跪不起,头点直言:“王上,您要臣如何,明说了吧!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好,爽快。”段素徽要的便是他这话,“原庸啊,你真乃孤王心腹之人,既然你对那侍婢情深一片,孤王又怎能不成全你二人呢?只是,毒杀君王乃滔天大罪,若找不到人顶罪,又如何能服悠悠之口?”
找人顶罪?
李原庸跪在原地,不敢擅自揣摩君心圣意,“不知王上以为,何人罪犯滔天?”
“孤王心腹之人自然知道这大理段氏王朝的心头大患姓甚名谁。”
李原庸叩首,起身这便告退。
十多天了,她被关在这里十多天了,没有人来提审她,也没有人来探望她。
是了,怎会有人来探望一个弑君杀主的罪人呢?
这是鬼字号地牢,这里关的只会是鬼和即将见鬼的人。
只是,王上亲手捉了她,何不直接断了她的罪,杀了她了事,还费心把她投到这里,一日三餐仔细照料着做甚?
蜷缩在不见天日的鬼字号地牢,她只盼速死,却又不知死期。
若说她还有什么期盼,便是盼着再见他一面。即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他们已然决绝,即便他叫她心灰意冷欲一死了却周遭所有的烦恼,她竟还盼着死之前再看他一眼。好带着对他最后、最深的记忆步下地府,转世投胎。
可连他,竟也不曾来———是王上不让,还是连他也将她全然遗忘?
她不知道。
满心里只是安慰自己,知道了又能如何?她选择了这条不归路,便断了所有的念想儿。
却听门外传来轻微稳重的脚步声阵阵,她打起精神,直觉地整了整耳鬓的乱发和臭味熏天的牢衣。
是他,她辨得他的脚步声,是他来了。
来送她最后一程吗?这样也好,能临死前再见上他一面,老天爷总算待她不薄,她这辈子算是活得知足了。
牢门被一层层打开,一道道枷锁松开的声响刺着她的心口。那是再见面的喜悦,也是送她进鬼门关的催促声声。
终于,他着官靴的脚定在她的面前。
顺着他的脚踝慢慢抬起头来,直望向他的脸庞———
“你消瘦了许多。”她言道。
她在这鬼字号的死牢里窝了这么些日子,倒还过得去,他在这朗朗晴空下,竟瘦了这许多,是为了她吗?几许期待涌上心头,她那稍稍平复的心又乱了。
李原庸半阖着眼睑垂下头来,她身在鬼字号地牢数日,竟还惦记他近日是否过得好?!她当真糊涂了吗?
“你……你怎么会干出这般傻事来?”要下毒,直接下剧毒,要了两位主子的命也还罢了。让人心口麻痹,却又要不了性命,她这下的是什么毒啊?“有人逼你的,是吧?”他早该料到了。
以她的性情,忍气吞声在后宫内苑苦熬了这些年,又怎会选在已然出宫过安生日子的这一天毒杀君王呢?
拉过她的双臂,他令她正视他的双眼,这才一字一句地同她说:“听着,密所笃诺,接下来的事你照我的话去做,完全照我的意思去办,好吗?就当我求你!”求你捡起自己的命,莫要一心盼死。
她空洞的双眸凝望着他,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李将军,李原庸,谢谢你来见我最后一面。这样就好了,放我去了吧!我苦熬了这么些年……已是太累了。”
太累了,她活着已经太累太累了。
叔公逼她,家人受迫,她至爱之人吝啬到连一个笑容都不曾给予,死,于她比活着容易太多了。
他却是不许。
“密所笃诺,你必须照我的话去做,必须!”他不理会她的决绝,只是照着他的心思命令她活下去,一直活下去,“说,是高相国命你在茶水里下毒,想借此控制大理段氏王朝,专权于天下———记着了吗?”
她歪倒在一边,连看都不曾看他一眼,他所说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吹进死牢里的清风,改变不了任何死亡的征兆。
下一刻,李原庸做出了此生他不曾想过的决定。
单膝点地,他跪在她的面前。
“今生,我的腿只跪过君王,再不曾向谁跪下。今日,我———李原庸跪在你———密所笃诺的面前。求你,我求求你,活下去———”
第七章 双拳出击同为卿命(1)
他跪了,为她,跪了?!
密所痴痴地望着跪在自己跟前的这个男人,脑海、心头,一片空白,什么都填不进去,装不进来。
李原庸只是说:“我知你钟情于我,我一直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对我的好,这些年,点点滴滴,便是石头也穿心了。我当真如此寡情薄意?不,我同你一样,我同你的心是一样的,于这偌大孤寂的王宫内苑,我也在等一个可以为我送饭的人,一个我一直期待却从未拥有过的家人。
“我不接受,我不接受你,你叫我如何去接受?你总是说我贵为将军,你只是个小侍婢,你配不上我。每每你如是说的时候,我都心生纠结,你叫我如何告诉你———不是你配不上我,是我不敢将你牵连进来。
“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吗?真正爱一个人,会以她的好为第一要则,宁可自己孤独终老,也不想坏了她唾手可得的安宁———我没有对你说过,你便是我后半生认定的,那个宁可自己孤独地死,也要保你一世安宁的那个人。
“身为宋国打入大理王朝的暗桩,你本是我的任务中必须要接近的人。可真的同你熟络了,我反倒想远离你。我不想你卷入这场万劫不复,我一直在躲你,一直在避你,不是不爱,相反,正是因为太爱了,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利用你?”
密所的手抚过他坚毅的面庞,从眉眼到鼻梁,再到那如刀刻出的唇角,停留在那里,好半晌,她的手都不曾舍得离开。
“你总说你嘴笨,不会说话,可这么笨的嘴一旦说起好听话来,比这世间所有的山盟海誓加起来还要动听。临死前能听到你说的这些话就够了,死都够了。只是,”她蓦然抽回自己的手指,颓然地向后退了几步,“太晚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她已经做了,弑君杀主,她已经做了,没得选了。
“不晚。”
若说他之前做的种种都是错的,从现在开始,他便只做这一件对的事,“我求过王上了,只要你……只要你将整件事推到一个人的身上,便什么都可以挽回。”
密所阖上眼沉吟了片刻,暗暗地吐出一个名字来:“高泰明———王上是想叫我把毒杀之事推到驸马爷身上,可对?”
李原庸默默地点了点头。
密所却冲着他死心地摇了摇头,“我不能,你知道的,我不能。你宁可死,也想要维护你珍视的人,我亦有同样的心。”
抓住她的肩膀,他用尽全力地摇晃着她,想叫她清醒,也想让自己从她的眼底看到一线生机,“可你不能死,我不允许你死,密所笃诺!”
他叫出了她的名字,连着她的姓,他就该明白,她这姓背后的意义。
“李原庸,你当是明白我的。我可以不顾彝族丧失百年的荣耀,可我不能不顾亲情,不能不顾我在这世间仅有的亲人。”
“可他顾你吗?”李原庸反唇相讥,“当年,本该是他进宫做宫人,可你替了他。今日,王上真正想铲除的人还是他,仍是你替他深陷牢狱———他顾你了吗?这么些年,他何时顾过你的安危?”
“可他,”密所悠然一叹,叹去了这些年的辛苦、哀怨和无尽的孤寂,“他是我哥啊!我唯一的哥。当年,即便二叔不撅了我手里的签,若我知道,他进宫会被骟了做宫人,我也会义无返顾地松开我阿母的手,走向长宫人。”
望着她,望着毫无生念的她,李原庸知道,王上给他的唯一这条路,不通,永远也不会通。
他可以做的,唯有再寻他法了。
直起身来,他最后看了她一眼,二话不说便走出了鬼字号地牢。
他走了,没有再回头。努力支撑着的密所再也撑不下去了,以手撑着地面,她依稀摸到一块布,从杂草堆里摸索出那东西,她定睛望去,竟是一块绞坏的荷包,看上去很是眼熟。
这……这不是那年她亲手绣了,又亲手绞坏的荷包嘛!
难不成是刚刚那一跪,使得这荷包从李原庸的身上掉了出来?
他一直带在身上,这些年这只荷包,他……一直带在身上?!
将那荷包紧紧地贴在心口,密所已是潸然泪下。
王上的路是堵死了,李原庸便去寻摸另一条道。
站在永耀斋里,场院里的这位贵主儿心情倒是大好,又是养鱼又是种草的,院央一派锦绣繁华。只是正厅堂上悬挂的那幅一人来高的丹青,提醒着宫内的众人,这曾是故去的耀王爷的殿阁。
“李将军今日兴致极高啊,竟有空来我这个闲着等死的地界转转。”
段负浪又在折腾他那盆破绿萝和萝下的几尾锦鲤,半盆子水换过来倒过去的,看得人眼晕。
李原庸刚想张口,段负浪忽撑起伞来,为那半盆绿萝、几尾锦鲤遮去了高照艳阳。为鱼遮阳,为萝挡光,李原庸暗道:“你还真有闲情雅致啊!”
段负浪却只是笑,“比不得哥哥你啊,心爱之人关在鬼字号死牢里,你还有心到我这里聊闲篇,可不是闲逸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