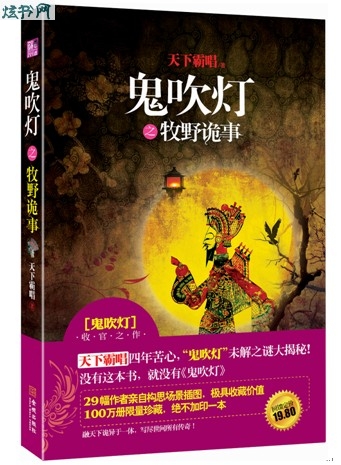牧野鹰扬-第2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友,想必已看到了牌示。”
“不错,在下已看见了,”简松逸微笑道:“的确在下是来贵寺访晤旧友的。”
“但不知施主访晤敞寺那位……”
“镜山方丈!”
僧人不由一愕,倏转笑容,含掌躬身道:“原来嘉客莅临,小僧失敬了。”立时肃容带路。
简松逸大模大样的走入禅堂。
小沙弥献上香茗退下。
中年僧人道:“施主稍待片刻,容小僧禀知方丈。”
“且慢!”简松逸道:“在下既来之就安之,禅师何必心急,在下还尚未请教禅师上下如何称呼?”
“不敢,小僧明性!”
简松逸颔首道:“取得好,明性见佛,好,好,禅师尚未询问在下来历姓名,如何道禀方丈?”
明性忙合掌道:“施主说的极是,敞寺就是未封闭一月,也难得一见香客,因此小僧到是忘怀了请教姓名来历,不过小僧可以将施主形貌年岁禀明,施主既然为方丈旧友,方丈那有不知之理。”
简松逸颔首道:“禅师说得委实有理,在下未免大惊小怪了,”说着拿起身旁几上香茗一饮而尽,连声赞道:“好香,好香,”茶盌复置几上时,拇指自盌顶一按,只见整个茶盌宛如嵌入一团湿麫内,了无声息,和茶几一般平。
明性禅师先见简松逸饮下一盌香茗,嘴角不禁泛出一丝狠谲笑容,倏即变为目瞪口呆,两条腿动弹不得。
简松逸目凝明性禅师,淡淡一笑道:“禅师为何不去禀明方丈?”
明性禅师如梦初醒,自知失态,忙合掌道:“施主武功精湛,已臻化境,小僧毕生罕睹,不禁神为之夺,告辞,”躬身而退。
无疑地,明性禅师怎会禀知镜山方丈,转至禅堂左侧从窻隙偷觑简松逸举止,暗暗骇异道:“茶内置有迷魂散,常人只饮一口,立时倒地昏迷不醒,就算他有精湛武功,也该倒下了,怎么……,”忖念之间,只见简松逸口中吐出一团黑烟,倏见黑烟外缘现出赤红火焰,嗤嗤燃烧,转眼黑烟烧得一乾二净,火焰随即消失无踪。
明性禅师看得瞪目结舌,久久才转身快步走向大殿而去。
简松逸则在禅堂内负手踱步,观赏壁悬山水画轴,名人墨宝。
身後忽生起一个宏亮语声道:“施主雅兴逸致不浅。”
简松逸似听而无闻,反负着双手拾指不着痕迹地弹出,口中低吟道: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
芜兵夜捉银胡绿,漠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羊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吟罢缓缓转过身子,只见一个身披袈裟六旬左右老僧,其後肃立着四个中年僧人,微笑道:“镜山方丈为何不亲自出见,要你们五人来此则甚?”
老僧道:“方丈命贫僧接引,施主请。”
简松遥朗笑道:“镜山,好大的架子,速去唤他来见我。”语气凌厉,气度慑人。
老僧不禁一怔,目中寒芒疾闪,沉声道:“施主真不随贫僧去见方丈么?须知来得去不得,拿下!”
简松逸笑容未减,反而大盛。
老僧猛然察觉身後四僧因何迟迟未出手将简松逸拿下,情知有异,掉面回顾,只见四僧如泥塑木雕一般,不知何时为人点住穴道。
忽闻简松逸冷笑道:“我不耐烦在此久候,速去通禀镜山方丈出见。”
老僧答道:“镜山方丈久未出寺云游,何况方丈也不识施主,故此疑施主来历可疑!”
“那么明性禅师为何在茶中施放迷魂散?”
“只因施主谓访晤旧友之故!”
“狡词强辩!”简松逸冷冷一笑道:“镜山不复记忆有我这么一个旧友,我却记得他,你速去禀告方丈,还带一句话,他必定前来。”
老僧道:“什么话,贫僧一定把话带到。”
简松逸道:“只有七个字,最难风云故人来。”
老僧不禁一怔,道:“施主武功文才虽无一不高,但这句话错了,贫僧记得要说最难风雨故人来。”
“没错!”简松逸斩钉截铁的道:“就照我所说的,他一定会记得,快去。”
老僧略一犹豫,应道:“贫僧这就去了。”
简松逸道:“但愿你能言而有信,勿像明性一般有去无同!”
老僧低应了一声:“是,”转身望了泥塑木雕般四僧一眼,心头不禁发怵,快步走出禅堂。
禅堂外花木丛中人影幢幢,一条灰影飞掠落在老僧身前,正是那一去不回的明性禅师。
明性禅师道:“师叔,这人被师叔拿下了么?”
老僧两道眉毛一皱,低声道:“他是独自一人前来么?”
“他是独自一人?”
“这就奇怪了,”老僧面色微变,道:“切勿轻举妄动,亦不可探视惊扰,俟老衲请示方丈後再说,”快步离去,走向方丈静室外竚足,宏声道:“师兄,小弟求见!”
“进来!”
老僧掀帘进入静室。
上盘膝坐着一霜眉银须,虎目狮鼻,貌像威猛森冷老僧,道:“广扬,此人拿下了没有?” 广阳答道:“未曾!”继敍出经过详情。
镜山方丈愕然问道:“他唤你第一句什么话?”
“最难风雨故人来!”
镜山方丈倏地离杨而起,鼻中冷哼道:“明性误事,快去,见了此人必须逆来顺受,出言恭谨,即使如此,老纳亦恐将不免受责!”
广扬不禁猛泛寒意。
镜山广扬两僧一前一后快步奔去,在未跨入禅堂前,命伏守四外人手速撤,留明性一人随他人见。
禅堂内简松逸仍自负手观赏四壁书画,吟哦不已,四僧依旧一如大雄宝殿四大天王一般,努目张嘴,泥塑未雕,一动不动。
镜山方丈暗暗震骇,合拳躬身道:“老衲来迟,请施主恕罪!”
简松逸转身朗笑一声道:“方丈何罪之有,到是虎溪禅寺即将毁于一旦,阁寺生灵无一幸免,未免可惜!”
镜山方丈不禁一愕,诧道:“施主之言老衲不解何意?”
“你我之间也不必打哑谜,何必方丈暗中苦苦摸索猜测在下来历。”简松逸目注了镜山方丈一眼,道:“方才亦约莫猜知在下是何许人?”
镜山方丈道:“老衲恭请谕示。”
“这就不敢方丈。”简松逸道:“你此刻也未必作得了主,速将大内奉命而来立其事者请来,危在眉睫,不能等到十五之夜。”
镜山方丈面色大变,忙道:“老衲遵命,明性,快去请宋大人。”
蓦闻禅堂外传来语声道:“宋某已来此等候宣召。”语声沙沉。
只见一背戴一双短戟,浓眉大眼老者,绕腮猬髭,约莫五旬上下,身高八尺,穿着一袭淡蓝色府绸长衫,举步之间矫捷无比。
简松逸淡淡一笑道:“尊驾定是铁戟温侯宋远谋了,你可是一人前来……亦或禅堂外尚怖伏得甚多人手?”
宋远谋面色一惊:道:“阁下姓赐告来历?”
“不!”简松逸寒声道:“在下未亮出身份前,一应无关的人手不准预闻,不然杀无赦,宋远谋,最好听话点!”
宋远谋一闻简松逸直呼其名,目中不禁泛出慑人寒芒,却又畏惧简松逸慑人气度,疑来头必然不小,不敢造次,倏又收敛。
忽见简松逸向窗外虚空一弹,只听传人惨噑一声,轰隆倒地。
宋远谋面色一变,转身向禅堂外跃去。
简松逸道:“方丈,明性等六位僧人虽奉你命不容可疑人物闯堂内,但也不得在未明白究竟前即贸然用毒和施展杀手,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这时宋远谋已自掠入,忙道:“阁下不可见罪他们,乃奉宋某之命而为。”
简松逸冷笑一声,五指一挥,道:“去罢,倘若再犯,决不轻饶。”
只见泥塑木雕四僧已然清醒过来,面现困倦委顿之色,广扬明性二僧猛感两臂酸麻乏力,不禁心惊胆战,广扬禅师道:“谢施主不杀之恩,贫僧等告退!”
俟广扬等六僧离去之後,宋远谋道:“现在阁下可亮出身份了!”
简松逸微微一笑道:“方丈,是否请暂避开!”
镜山方丈闻言不禁望了宋远谋一眼,见宋远谋点了点头,忙合掌躬身道:“老衲告退!”
简松逸伸手入怀,取出两物,递与宋远谋,道:“你拿去瞧吧!”
宋远谋托在掌心,仔细一瞧,不禁吓得魂不附体,将二物恭敬放在桌上,跪伏在地拜了九拜,又面向简松逸跪下,道:“属下该死!”
简松逸将二物收回怀内,伸手搀起宋远谋,道:“你我不相统属,何必行此大礼。”
宋远谋惶恐答道:“见牌如见君,见君不拜便是一项大不敬之罪!”
简松逸微笑道:“由你,由你,本来我也不愿多事,萨督使虽负全责,但其下各有主其事者,彼此亦不相涉,制度虽好,但也有缺点,好,这些暂且不提,十五月圆含鄱口後山之约是你主其事么?”
“正是!”宋远谋道:“但属下却不露面。”
简松逸长叹一声道:“你露不露面都是一样难逃死亡之祸。”
宋远谋大惊道:“大人是否查明了什么?不知可否明谕属下如何趋吉避凶?”
简松逸摇手微笑道:“别急,你且坐下共商如何?”
宋远谋告罪坐下。
简松逸道:“如今明君即位,究竟年幼,朝中政务均由几个托孤大臣把持,暗中相互倾轧不已,外患亦有前明志士及江湖英豪奉明正朔誓言光复神州,复兴延平郑氏互通声气,并非疥癣之疾,不可不防,不过……”说时望了宋远谋一眼,接道:“大内均遗得有人在他们巢穴内卧底,对方一举一动,不说了如指掌,却可察知其举止大概。”
宋远谋道:“大人说得极是!”
简松逸朗笑道:“但对方也遣得有人在咱们中卧底,可说是无孔不入,最令人困扰的就是那些黑道凶邪,既不帮咱们这边,也不相助对方,挑拨启事,图获渔翁之利。”
宋远谋忖思:“他告诉自己这些是为了什么?”口中却应道:“大人说的极是!”
简松逸似瞧出宋远谋的心思,笑道:“你不要认为我说些都是不相干的话,其实兹事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知道么?据我所知,今儿十三,明日十四,对方在明晚统大举侵袭虎溪禅寺先纵火烧毁,後再逐个歼杀!”
宋远谋大惊失色道:“对方是谁?请大人明告,是否是徐三泰程乃恭等人?”
简松逸道:“并非我故作神秘,要是徐三泰程乃恭那就好办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咱们长话短说,你知道么?危肃及侯世流如今身在何处?”
宋远谋惊道:“属下派他们两人办事去了!”
“不幸他们被人劫走了!”简松逸冷冷一笑道:“我追踪而去,当时因不明究竟,故而让他们兔脱,归途中但却无意偷听得有数人在密林中低声谈话,不敢逼近,却听得他们十四晚大举进袭。”
宋远谋面色频频变异,略一犹豫道:“恕属下胆大放肆,有几处疑点尚请大人明示。”
简松逸微微一笑道:“你胸中仍有疑虑,我均已知道,是否想问我不明白究竟,怎么知悉危肃及侯世流二人被擒劫走是么?”虽是谈笑从容,却语音寒沉。
宋远谋悚然一震,几乎吓得一身冷汗,立起躬身施礼道:“大入料事如神,属下无状该死!”
只见简松逸喟然叹息道:“我不是说过几句话么?谅你必未仔细倾听,一则对方有奸细卧底,再说我不愿多事,无意听得其中些微隐秘,更那些凶邪怪异心怀叵测,煽火挑衅,移祸东吴,从中渔利,如不出我所料,劫去危肃及侯世流那帮人必是他们。”
宋远谋暗暗心惊,躬身道:“请示大人,属下此刻应如何处理?”
“主其事者是你不是我,无法越俎代庖,有话说得好,目睹犹恐是假,耳闻岂可当真,我本急偶闻,须防误中他人诡计,不过……”简逸语声突变低微,道:“只严密注意镜山方丈及叫什么杜……哦,是了,可是杜秋藻,其余的事你自己决定好了,最重要的不可向任何人吐露我的来历,即使萨磊也不可,否则杀无赦!”
宋远谋忙跪伏在地,道:“属下不敢!”心中忖念:“此人必是王公贝子贝勒之流,不怒而威,否则怎有皇上“如朕亲临”令牌!”
“起来,我不愿久留,”就在宋远谋起身之际,附耳密语如何如何。
宋远谋连连答道:“属下遵命!”
简松逸飘身走出禅堂,目睹镜山方丈立在青石小径上,似久候不耐,当即微笑道:“打扰了!”身如行云流水而杳。
宋远谋在禅堂内不停地自责,喃喃自语道:“该死,此人如非王公贝子贝勒,必也是皇亲国戚,如何自称属下,应该自称奴才,那么自己如何称呼他,爵爷或是千岁,